当高举黑太阳大旗奔跑在街头的热血青年在循环往复年复一年的“运动”中年华老去,变成了雪地里如服丧的队伍般动作迟缓表情麻木的中年人;年轻的男孩们对成年政治世界毫不关心满脑子只有白花花的大腿;饱涨着原始的残暴性欲的新生的底层在考场的讲台上强暴文绉绉的永远保持着高雅的中产少女的幻想;淫靡低俗的春歌是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的底层人民被挤压至变形的欲望的释放,是矿工男孩在矿井里密会的那个早已死在他们相遇之前的女孩的幽灵,是开始就不允许存在的东西;因而底层的少女在文质彬彬的温和中产们其乐融融的反越战趴体上因一首春歌被当作妓女轮暴;但是看似狂妄躁动的少年们却在得到“同意”之后,面对在梦中肆意糟蹋的少女的胴体与泰然自若的眼神,依然局促,困顿,迷茫——“来真的吗?”. 还是熟悉的大岛渚母题:爱是我所剩的最后的反抗.
还是熟悉的大岛渚母题:爱是我所剩的最后的反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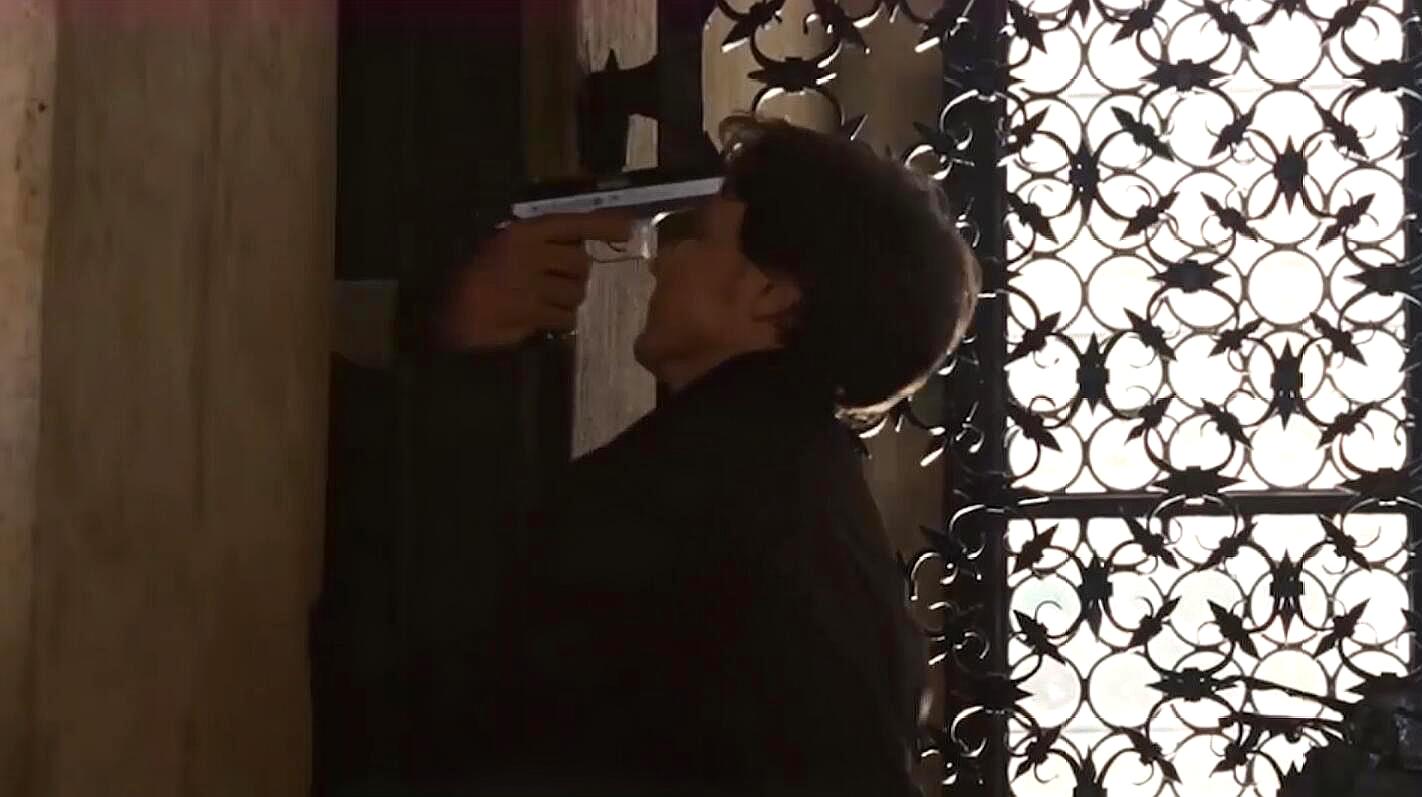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永远有种差了那么一口气的感觉,在这个看似准确而老练的叙事型镜头之内有太多话没说完或过分煽情的细节欠缺.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永远有种差了那么一口气的感觉,在这个看似准确而老练的叙事型镜头之内有太多话没说完或过分煽情的细节欠缺. 运沙填海即为“幻土”,郭月的角色之嘴道出这片土地“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电影勾勒了一个被镜头所记录的无名区,站立之上的是一群亦真亦假、似梦似真的形象、人物关系和谜语叙事.
运沙填海即为“幻土”,郭月的角色之嘴道出这片土地“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电影勾勒了一个被镜头所记录的无名区,站立之上的是一群亦真亦假、似梦似真的形象、人物关系和谜语叙事. 抛开这群亚洲新导演都喜欢的“永远睡不醒”的电影表现或叙事风格,《通缉犯》比起《通缉犯》和《通缉犯》至少在讨论(并置)了一些切实现实内容,投射了一些新加坡移民的人文关怀,但这场存心不愿意醒的睡眠、不让人解开的谜语与其说是神秘倒更像一种装睡的故弄玄虚.
抛开这群亚洲新导演都喜欢的“永远睡不醒”的电影表现或叙事风格,《通缉犯》比起《通缉犯》和《通缉犯》至少在讨论(并置)了一些切实现实内容,投射了一些新加坡移民的人文关怀,但这场存心不愿意醒的睡眠、不让人解开的谜语与其说是神秘倒更像一种装睡的故弄玄虚. 究其原因还是叙事技法略显生涩,有些台词看似是欲言又止的谜面实则是矫情,有些应该暧昧温柔的地方有种不合时宜的情色感.
究其原因还是叙事技法略显生涩,有些台词看似是欲言又止的谜面实则是矫情,有些应该暧昧温柔的地方有种不合时宜的情色感. 工业和移民劳工问题,导演至少打开了另类的南洋风貌.
工业和移民劳工问题,导演至少打开了另类的南洋风貌.
电影
剧集
综艺
动漫
专题
明星